ChongMingS.COM崇明網訊 日前,勞動者封先生來到勞動報反映他所遇到的波折經歷。他稱自己在同一家單位的安排和管理下,在同一個地點、同一崗位上連續工作,一直以為與該單位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然而在此過程中,與他簽訂合同的卻是另外的單位,實際上只負責為其繳納社保。幾年里,幾段勞動關系中的甲方不斷變化,讓他感覺混亂、分辨不清,尤其是他打官司時,單位出示的《辭職信》,導致他輸掉官司不服,也讓他不解和無奈。
實際工作單位與簽合同單位不一致
2012年3月,封先生通過招聘進入上海A公司,同年5月被派往上海一家機械廠項目組從事協力保產工作,2014年2月被調至B公司從事現場管理工作。他與A公司自2012年3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訂立過三份一年期的《外聘人員協議書》。
2014年10月之前,封先生的勞動關系仍保留在C公司,為公司協保人員。后因C公司改制,雙方協議解除了勞動關系。封先生事先向A公司反映了情況,相關人員承諾說結束前一段勞動關系之后,幫助他辦理進入A公司。封先生也向A公司人事部進行了情況說明。解除了前一段勞動關系的封先生等了一個多月后,卻被A公司人事部告知,由于上級集團有規定,從集團下屬單位出來的人員,不可再進入集團其他下屬單位,而封先生此前公司和A公司均為這家集團下屬企業,因此無法與A公司建立勞動關系。之后,公司與封先生商議,為確保利益不受影響,社保關系放在D公司,由D公司為其代繳社會保險等費用,工資、福利、技術培訓等仍由A公司承擔。
封先生回憶,在2014年12月,他與D公司簽訂了為期兩年的勞動合同。他說記得當時合同時限為2014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0日,合同里沒有約定工資、上班地點、崗位等內容,簽好后就被收走了,自己手上沒有這份合同,并且單位始終不肯出示這份合同。封先生表示,這個所謂的D公司,從來沒有見過其管理人員,也找不到具體地址,也不清楚是否有相關資質……
權益還沒計算清楚,勞動關系一變再變
封先生反映,按照B公司管理要求,一般需要24小時有人在現場,自己作為其中一名負責人,經常周末也要到廠里加班。他說,工資的構成是基本工資、崗位工資、技能工資等,單位另外計算支付加班費。但在2014年11月以后,工資都是以現金形式簽字發放,每個月大概五千七八百元。自2014年11月至2018年1月公司方面從沒安排年休假。
2015年9月的一個周六,廠里設備突發故障,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是有供應商提供備件的,但遇到周末沒辦法及時解決,于是封先生自己到市場上買配件。當時天在下大雨,封先生途中騎電瓶車打滑摔倒在地,左手劇烈疼痛。跑了兩家醫院,被診斷為左手骨折,醫生建議做手術。后來D公司幫其申請工傷認定,由原上海市閘北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于2015年12月7日出具《認定工傷決定書》,對封先生在2015年9月12日騎車外出采購機電產品途中不慎摔倒致傷,造成左肱骨上端骨折,認定為工傷。“兩區”合并后,上海市靜安區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于2016年5月9日出具《初次(復查)鑒定結論書》,確定封先生因工致殘程度九級,之后他領取了一次性傷殘補助金。
封先生稱,工作至2017年上半年,A公司進行了改制。6月初,D公司方面要求封先生寫辭職報告結束勞動關系,再跟改制后的公司簽合同,遭到封先生拒絕。他月末領工資時發現6月19日D公司已辦理了退工手續。封先生收到單位退工證明:自2015年1月進單位工作,現于2017年5月31日合同終止。
2017年7月,封先生又在A公司領導安排下,與改制后新成立的新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合同約定期限至“B公司設備維保項目工作完成”,工作內容、崗位、地點、待遇都沒變。到了2018年1月,項目完成后,封先生與新公司勞動關系終止,并獲得了相應的經濟補償金,雙方沒有任何爭議。但是當他提出2014年11月至2017年6月這段時間的經濟補償時,沒有哪家單位給出答復、肯負責任。在申請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工傷待遇時,也沒有哪家單位肯為給他開具證明、承擔責任,這讓他十分失望。
自認權益受損與單位打起官司
封先生認為,自己從2012年3月起一直是給A公司工作的,與之有事實勞動關系。期間,簽合同被轉來轉去,都是被迫安排的,造成自己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權益受損。他說,向法律部門提供了以下材料,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期間,工資簽收復印件證明A公司發放工資。《情況說明》、短信截屏組,證明向A公司說明其與C公司解除勞動關系的事實。2017年1月至6月的出勤考評表、備忘錄、回復、情況說明、回顧保養實施情況表一組。2015年2月、2016年1月、2017年1月、2018年2月現場設備維修協作會議記錄等。他覺得,簽訂合同的D公司從未進行過管理、從未安排工作,這些材料充分說明自己始終是為A公司工作的。
自認為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封先生在2018年5月5日向上海市靜安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向A公司提出相關主張,卻被告知應該向D公司主張,隨后撤訴。又于2018年6月11日提起仲裁請求,10月28日收到裁決書,全部請求未被支持。
封先生很是無奈,遂起訴至靜安區人民法院。封先生提出的訴訟請求包括:要求D公司支付未簽訂勞動合同雙倍工資差額、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工資差額、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休息日加班工資差額、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應休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資等。
案件進展▲
封先生決定繼續上訴
庭審中,D公司拿出了封建林簽名的《辭職信》,該2017年5月31日簽署的《辭職信》內容為,封建林于2017年5月31日正式辭職并離開D公司,同時也與D公司結清了所有相關的收入、福利、報銷及其他相關手續,相互之間已無任何拖欠。公司養老保險賬戶轉出申報表及核定表證明,為封先生繳納社會保險至2017年5月。公司另辯稱,封先生離職后又與其他公司建立了勞動關系,且在一年內沒有主張過任何權利,訴請已經過了訴訟時效。封建林向記者表示,確認《辭職信》上簽名是自己的,但是又稱自己沒見過該份《辭職信》,自己也不清楚是否簽過。
法院認為,根據D公司出具的《上海市單位退工證明》和有關部門出具的《認定工傷決定書》、《鑒定結論書》以及簽字的《辭職信》,認定雙方于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存在勞動關系。最終,法院確認《辭職信》的真實性,鑒于雙方之間不存在任何費用拖欠,且封先生申請仲裁時已超過法定的申請時效,對其全部訴訟請求均不予支持。封先生準備提起上訴。
專家觀點▲
勞動關系建立的要素需認清
實踐中勞動者遇到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為勞動者保管檔案、代為繳納社會保險,但無實際用工行為,安排勞動者工作卻另有單位。對此現象,上海市律師協會勞動法業務研究委員會干事、上海祺道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宋玲娣分析認為,在此種情形下,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與實際使用勞動者的單位不一致,發生糾紛時,容易相互推諉,不想承擔責任,導致勞動者在申請仲裁時不知應將哪家公司作為被申請人。依照《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第二十五條的規定,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和實際使用勞動者的單位不一致的,用人單位可以與實際使用勞動者的單位約定,由實際使用勞動者的單位承擔或者部分承擔對勞動者的義務。實際使用勞動者的單位未按照約定承擔對勞動者的義務的,用人單位應當承擔對勞動者的義務。
從封先生與D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保事宜等可知,封先生建立勞動合同的合意相對方系D公司,也知曉其工作內容、崗位、地點、待遇均參考A公司,但根據《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規定,系兩單位對勞動者承擔義務的規定,若雙方有該約定從約定,若無相關約定,則應由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承擔對勞動者的義務。
在勞動爭議糾紛中,對雙方之間法律關系性質的認定即雙方是否建立或存在勞動關系,直接決定了雙方權利義務的內容。認定勞動關系的依據是什么呢?根據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的規定以及相關司法實踐,勞動關系是否成立或存在一般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考察:(1)用人單位和勞動者是否符合法律、法規的主體資格;(2)勞動者是否向用人單位提供有報酬的且為用人單位業務組成部分的勞動;(3)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規章制度是否適用于勞動者,即勞動者是否接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和工作安排。那是否符合該規定即是勞動關系呢?并非如此,勞動合同是一種特殊的合同關系,基于其合同概念的基礎,仍需要雙方均有建立之合意,即勞動合同關系應當以“雙方是否存在建立勞動關系的合意”為基礎,若無該合意,即便符合以上規定也難以認定為“雙方建立勞動關系”。
同時,書面的勞動合同是勞動合同內容賴以確定和存在的方式,即勞動合同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一致的表現。故,對于勞動關系的認定,若有勞動合同的情形下,一般以勞動合同為準,除非有證據證明該書面勞動合同存在無效的情形。
留意仲裁時效爭取有利時間
該案中關鍵的一點是,“封先生申請仲裁時已超過法定的申請時效”。勞動爭議仲裁時效,是指仲裁案件當事人因勞動爭議糾紛要求保護其合法權利,必須在法定的期限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如無法定仲裁時效中斷、中止事由,法律規定消滅其申請仲裁勝訴權的一種時效制度。作為勞動者,十分有必要了解一下勞動爭議仲裁時效制度,避免疏忽大意導致合法權益“過期”。
勞動爭議仲裁時效制度的建立,一方面督促當事人及時地行使權利,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因當事人怠于行使權利致使仲裁時效期間屆滿,當事人喪失仲裁勝訴權,也有助于盡快穩定社會秩序,減少社會糾紛。這種制度,在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領域都有規定,相當重要。《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前款規定的仲裁時效,因當事人一方向對方當事人主張權利,或者向有關部門請求權利救濟,或者對方當事人同意履行義務而中斷。從中斷時起,仲裁時效期間重新計算。”該款規定了仲裁時效的中斷,中斷之后,期間重新計算。第三款規定“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當理由,當事人不能在本條第一款規定的仲裁時效期間申請仲裁的,仲裁時效中止。從中止時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時效期間繼續計算。”該款規定了仲裁時效的中止,中止原因消除后,期間重新計算。第四款規定“勞動關系存續期間因拖欠勞動報酬發生爭議的,勞動者申請仲裁不受本條第一款規定的仲裁時效期間的限制;但是,勞動關系終止的,應當自勞動關系終止之日起一年內提出。”該款對勞動爭議仲裁時效期間一年的規定作了區分,即勞動關系終止的,提起勞動仲裁申請應在勞動關系終止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勞動關系存續的,因勞動報酬發生爭議的,不受一年訴訟時效的限制。
針對勞動仲裁時效制度,勞動者在維權上可通過以下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勞動者在職期間,因勞動報酬與單位發生糾紛,雖不受一年仲裁時效的限制,也應及時向單位主張。因一旦勞動關系終止,就要適用一年訴訟時效了。勞動者在離職后,因與單位發生勞動糾紛,應及時與單位交涉;可以在和單位主管人員進行交涉時,在不侵犯第三人合法權益時,采用錄音、錄像的方式取證;可以對主張的權益采用書面形式郵寄單位,保留文書復印件及快遞單;可以委托律師發出律師函;可以向勞動監察部門投訴反映;可以向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請。通過留下這些“痕跡”的方式,來證明自己對權利的積極主張,觸發仲裁時效的中斷條件,從而保障權利免受仲裁時效的限制。
簽署離職報告需謹慎
宋玲娣律師分析,根據《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單位終止勞動合同,如果員工沒有違法行為,需要按照標準支付補償金。但如果因員工個人原因辭職,可能無法獲得經濟補償金。因此,勞動者離開單位的原因非常重要,在辦理離職時,簽署任何文件時都要留心,以免為后續維權造成障礙。
一般單位為了避免事后被追責,常常會在勞動者離職時注明類似“……全部結清、與單位無任何糾紛”內容,或者要求勞動者填寫“個人原因”,證明辭職是員工本人提出的,如果單位做法沒有違法之處,就不需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賠償金。裁判機關審理此類爭議時,會審查相關證據材料,而員工簽署的文件系員工的意思表示的文字呈現。如果用人單位確有證據證明勞動者離職的理由是由于個人原因(比如辭職書、解除通知書),裁判機構會認定該理由為真正辭職理由。
因此,本案中封先生簽署的《辭職信》很關鍵,他雖稱未簽過,卻也沒有證據足以證明其主張,如果一直無法提供證據,則要承擔不利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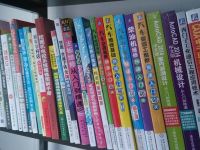












網友回復